據記者了解,山東省《關于開展儲能示范應用的實施意見》將于近期出臺,今年2月,該省還曾印發《2021年全省能源工作指導意見》,提出建立獨立儲能共享和儲能優先參與調峰調度機制。
山東并非個例,雖然各省市紛紛出臺相關政策支持儲能產業發展,但從目前公布的全國和各省開發建設方案來看,儲能義務集中在了發電側,且責任主體并未局限在新增項目當中,而是在向存量項目蔓延。
是否必要?
當前,發展儲能的核心原因有二:對內,提升電能質量;對外,降低限電風險,發電側儲能可以起到哪些作用?是否存在必要?
儲能行業資深投資專家張大鵬認為,發電側配儲能,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發電裝置配儲能核心目的就是為了緩解棄風棄光、改善可再生能源發電質量,最大限度提升新能源發電的消納水平,另外,儲能裝置本身除了可以實現上述功能外,還可以參與地方電力現貨市場交易,滿足區域電力靈活性調度需求。
“個人認為,當前地方政府強制發電側配備儲能,主要還是為了加快可再生能源快速發展的‘緩兵之計’,地方新能源產業的發展不可能等待電網側儲能發展成熟后再追趕,因此發展分布式電化學儲能裝置就是當下最適合的解決方案。”張大鵬說。
盛世景資本智造中國投資總監吳川告訴記者,發電側配儲能的核心目的是實現電源的可調度性,包括調頻和調峰兩種能力的優化。目前,傳統電源側重輔助調頻,新能源側重平滑和彈性輸出。“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,‘儲’本身就是能源系統中的必然結構,未來也不可或缺。”
是否對等?
記者發現,目前配置儲能的權利義務明顯不對等。回顧最早期的新疆項目試點政策,增加儲能后會有保障小時數增加的回報,但現在梳理各地的政策,強配儲能后的權利只字未提,比如,沒有做出新增平價項目能夠簽署連續20年PPA的承諾、沒有配儲能項目必然不限電、儲能設備會被按照要求逐日調用、不再需要分攤調峰費的承諾。
張大鵬認為,當前階段發電儲能投資人還是相對弱勢。“主要是由于發電側儲能的商業模式都是由三方投資的收入分成模式,其并網、結算都需要借助電廠的‘通道’,如電廠消極應對、拖欠費用、或因其他原因長時間停機都將對投資人帶來不利影響。”
在吳川看來,2019年以來,光伏和風電的發電成本接近火電,產業邏輯發生了變化,疊加“30·60”雙碳目標政策支持,行業熱情非常高。但是,近來,各地發布了對新能源配儲能的要求,規定了配置儲能的義務,雖然能夠提高新能源電的質量,卻推高了新能源發電成本。目前,政策的制定滯后于產業發展,權責利的劃分不夠明晰,“權利”滯后于“義務”,會損傷投資者的熱情。
是否可行?
在傳統能源體系中,煤炭、油、天然氣等化石燃料承擔“儲”的功能,向電網輸出“二次電力”,是“儲+發”的一種電源形式。未來光伏、風電等“一次電力”成為主要電源,電源側必將演化為“發+儲”的電源形式。“儲”的內涵也從儲存化石燃料演化為“儲電”。
吳川表示,現階段,鋰電池儲能輔助調頻和新能源并網,已經驗證了儲能在發電側的功能。但是發電側配儲能仍需面臨技術和政策兩大難點,首先,低成本的中等規模儲能技術和高可靠性輔助調頻儲能技術尚不成熟,需要盡快示范和推廣;其次,各種形態的儲能方式加入電網,對并網和調度提出更高的要求,電網也需要進行裝備和技術革新。同時,“儲能”方式改變,電網參與主體的關系也發生了改變,相關政策需要跟上。
不過就現階段發電側配儲的時間節點來看,張大鵬建議,在當前各地紛紛出臺強制配儲的背景下,發電側最關鍵的是需要在成本控制的同時,防范儲能產品質量、安全風險,不斷優化提高儲能裝置運營效率。
“另外,要積極參與區域電力現貨市場交易,增加儲能裝置盈利能力,培養現貨市場交易團隊,積極探索創新‘新能源+儲能’合作模式,如在區域內建立大規模獨立儲能電站,通過與獨立儲能電站租賃容量、現貨交易等多種合作方式,減少自身投入,最大程度發揮儲能裝置在區域內的‘海綿’效應。”張大鵬說。
原標題:既沒有身份也沒有權利 三問發電側配儲
山東并非個例,雖然各省市紛紛出臺相關政策支持儲能產業發展,但從目前公布的全國和各省開發建設方案來看,儲能義務集中在了發電側,且責任主體并未局限在新增項目當中,而是在向存量項目蔓延。
是否必要?
當前,發展儲能的核心原因有二:對內,提升電能質量;對外,降低限電風險,發電側儲能可以起到哪些作用?是否存在必要?
儲能行業資深投資專家張大鵬認為,發電側配儲能,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發電裝置配儲能核心目的就是為了緩解棄風棄光、改善可再生能源發電質量,最大限度提升新能源發電的消納水平,另外,儲能裝置本身除了可以實現上述功能外,還可以參與地方電力現貨市場交易,滿足區域電力靈活性調度需求。
“個人認為,當前地方政府強制發電側配備儲能,主要還是為了加快可再生能源快速發展的‘緩兵之計’,地方新能源產業的發展不可能等待電網側儲能發展成熟后再追趕,因此發展分布式電化學儲能裝置就是當下最適合的解決方案。”張大鵬說。
盛世景資本智造中國投資總監吳川告訴記者,發電側配儲能的核心目的是實現電源的可調度性,包括調頻和調峰兩種能力的優化。目前,傳統電源側重輔助調頻,新能源側重平滑和彈性輸出。“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,‘儲’本身就是能源系統中的必然結構,未來也不可或缺。”
是否對等?
記者發現,目前配置儲能的權利義務明顯不對等。回顧最早期的新疆項目試點政策,增加儲能后會有保障小時數增加的回報,但現在梳理各地的政策,強配儲能后的權利只字未提,比如,沒有做出新增平價項目能夠簽署連續20年PPA的承諾、沒有配儲能項目必然不限電、儲能設備會被按照要求逐日調用、不再需要分攤調峰費的承諾。
張大鵬認為,當前階段發電儲能投資人還是相對弱勢。“主要是由于發電側儲能的商業模式都是由三方投資的收入分成模式,其并網、結算都需要借助電廠的‘通道’,如電廠消極應對、拖欠費用、或因其他原因長時間停機都將對投資人帶來不利影響。”
在吳川看來,2019年以來,光伏和風電的發電成本接近火電,產業邏輯發生了變化,疊加“30·60”雙碳目標政策支持,行業熱情非常高。但是,近來,各地發布了對新能源配儲能的要求,規定了配置儲能的義務,雖然能夠提高新能源電的質量,卻推高了新能源發電成本。目前,政策的制定滯后于產業發展,權責利的劃分不夠明晰,“權利”滯后于“義務”,會損傷投資者的熱情。
是否可行?
在傳統能源體系中,煤炭、油、天然氣等化石燃料承擔“儲”的功能,向電網輸出“二次電力”,是“儲+發”的一種電源形式。未來光伏、風電等“一次電力”成為主要電源,電源側必將演化為“發+儲”的電源形式。“儲”的內涵也從儲存化石燃料演化為“儲電”。
吳川表示,現階段,鋰電池儲能輔助調頻和新能源并網,已經驗證了儲能在發電側的功能。但是發電側配儲能仍需面臨技術和政策兩大難點,首先,低成本的中等規模儲能技術和高可靠性輔助調頻儲能技術尚不成熟,需要盡快示范和推廣;其次,各種形態的儲能方式加入電網,對并網和調度提出更高的要求,電網也需要進行裝備和技術革新。同時,“儲能”方式改變,電網參與主體的關系也發生了改變,相關政策需要跟上。
不過就現階段發電側配儲的時間節點來看,張大鵬建議,在當前各地紛紛出臺強制配儲的背景下,發電側最關鍵的是需要在成本控制的同時,防范儲能產品質量、安全風險,不斷優化提高儲能裝置運營效率。
“另外,要積極參與區域電力現貨市場交易,增加儲能裝置盈利能力,培養現貨市場交易團隊,積極探索創新‘新能源+儲能’合作模式,如在區域內建立大規模獨立儲能電站,通過與獨立儲能電站租賃容量、現貨交易等多種合作方式,減少自身投入,最大程度發揮儲能裝置在區域內的‘海綿’效應。”張大鵬說。
原標題:既沒有身份也沒有權利 三問發電側配儲
 微信客服
微信客服 微信公眾號
微信公眾號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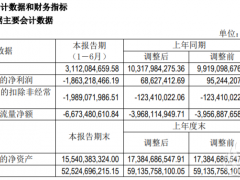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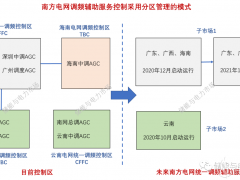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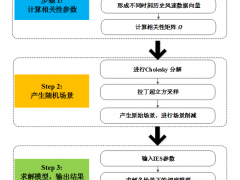
0 條